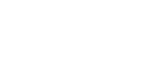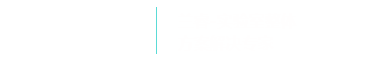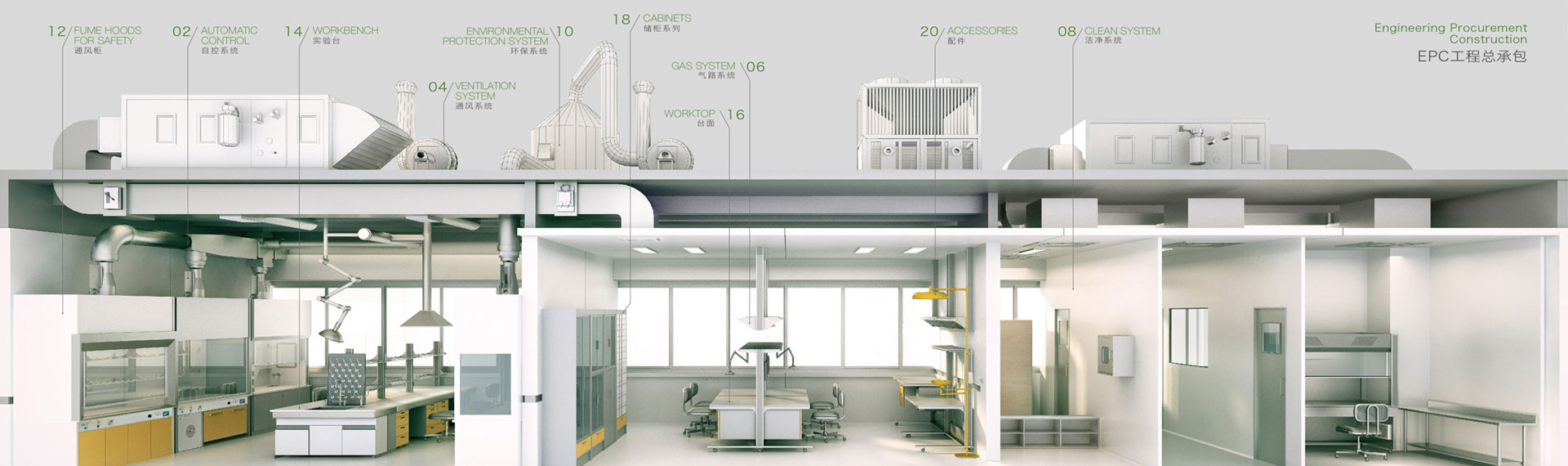关于韩春雨的科研问题一直处于舆论的旋涡 。“结果”公布后 ,与预料的相似 ,这一调查和处理结果很难服众 ,无论是学界还是公共领域 。“结果”表述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 ,“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 ,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
“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指的是韩春雨团队之前发表的研究结果不能重复 ,“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是指该团队并非有意造假 。
问题也出在这两个有相互关系的因素上 。研究结果不可重复是否为造假或学术不端行为 ,现在恐怕还有一定的争议 ,但即便认定是造假 ,在人们看来 ,“结果”也是在为韩春雨团队缓颊 。无主观造假 ,就意味着不是有意 ,而是无意 。那么 ,是否存在有意和无意造假 ,如何区分这两种造假 ,以及区分后应否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尤其是后者 ,让人们感受到与国外的学术造假所进行的严厉惩处有天壤之别——例如韩国的黄禹锡、日本的小保方晴子——有息事宁人或姑息养奸之嫌 。
爱游戏·全站APP登录入口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认为 ,“要么造假要么不造假 ,哪有主观不主观之分” 。实际上 ,在研究中学术造假或学术不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尤其是在研究结果不可重复之上 。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当然是“有意”造假 ,前者是在两篇论文中的所有图像和数据都伪造 ,后者是在论文中篡改图像 。
而研究结果不能重复则甚至已经是今天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情况 。早在2011年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开放科学中心的心理学教授布莱恩·诺赛克(Brian Nosek)等人牵头 ,招募全球250多名科学家参与 ,对2008年发表在3家顶级心理学期刊上的100项心理学研究结果进行重复研究 ,2015年该项重复性研究完成 ,结果仅有39项研究结果可以再现 ,61项研究结果无法重现 ,不可重复率达到61% 。
此后 ,诺赛克等人又再次组织了由多个国家研究人员参与的一次重复性研究 ,对2010-2015年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期刊上的21篇心理学论文的结论进行重复性研究 ,结果是 ,38%的结果不可重复 。这一重复性研究结果已经在线发表在2018年8月27日的《自然》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期刊上 。
不仅是心理学研究结果有很高的不可重复比率 ,就连生物医学研究也位居不可重复率的排行榜的高位 。拜尔医学的研究人员对发表在世界著名科学期刊上的67个实验项目的数据进行重复研究 ,结果显示 ,仅有21%的项目(14个)可重复 ,高达65%的项目(43个)数据不能重复;另有7%的项目(5个)能重复主要数据 ,4%的项目(3个)可重复部分数据 。
而且 ,上述研究都是发表在今天影响因子高的主流期刊上 ,包括《细胞》(Cell)、《自然》(Nature)、《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和《科学》(Science) ,即CNPS 。不仅如此 ,不可重复的科学研究结果几乎遍布于所有学科 。一项研究表明 ,今天在全球一流的学术期刊CNPS发表的论文的结论至少有一半不可重复和检验 。
研究结果不能重复固然有很多原因 ,但在诺赛克看来 ,主要原因还是源自结果的“假阳性”和“膨胀效应大小” 。简单地说 ,前者就是假结果 ,后者则是夸大结果 ,这两者都牵涉到是否主观(有意)还是无意 。
严格地讲 ,诚实的学术研究是 ,研究者应当对首次结果进行多次重复验证后才予以发表 。但是 ,实际情况是 ,研究者并没有经过自己的重复试验或研究就急匆匆地发表结果 ,或即便重复检验了却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发表 。表现为 ,一是首次研究结果就出现了研究者所期待的甚至远远优于期待的结果 ,于是未做验证重复研究就发表研究结果;另一种是试验了多次 ,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假阳性结果 ,只是研究者并不知情 ,便予以发表 ,这种情况如同一位病人在同一所医院就诊 ,多次检查的结果都一样 ,但换了另一所医院检查 ,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重复研究需要其他人和其他机构来进行的根本原因;还有一种是进行了多次试验 ,每次的结果都有差异 ,但是 ,为了讲一个好的故事 ,研究者选择发表最好的结果 。
这些情况的发生缘于众所周知的动机 ,一是获得科学研究的首先发现权 ,二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包括获取巨额经费、得到高薪职位、掌管科研机构和提高声誉 。
研究结果不可重复与数据、图片以及研究过程的蓄意造假 ,如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的有意伪造图片和数据 ,以及没有进行试验说成是进行了试验 ,是有一定区别的 。但是 ,如果认定研究结果不可重复就是造假 ,而且造假就是造假 ,难以和根本不可能区分主观(有意)和客观(无意) ,那么 ,当今世界的科学研究就必须面临一半甚至超过一半是造假的现实 。
如此 ,不仅是学界 ,也是全社会需要面临的极大挑战 ,如何对待和处置科学研究中一半的甚至更高比例的不可重复结果(结论) ,也即造假?